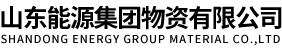二十二岁的隆冬,济南站台,大雪。我手中紧攥的,不过是一张薄纸般的车票。绿皮火车喘息着,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青涩懵懂的身影。四十八小时在铁轨的咣当声里流逝,煎饼的咸香,邻座老工长脸上沟壑纵横的矿区往事,是这段漫长旅行的注脚。那时天真地以为,“远方”只是一个目的地,却不知它早已在暗中揉皱了命运的图纸。
抵达新疆伊宁矿区时,零下十摄氏度的寒风像刀子般割着脸。矿区的生活简单得近乎荒凉:宿舍的暖气片永远不够热,食堂的土豆炖白菜却总飘着香气。我和同事们挤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核对数据报表,稿纸上的墨迹被暖气烘得发皱。深夜加班时,远处矿井的探照灯刺破黑暗,像一盏永不熄灭的灯,照映着我们的青春。
告别天山脚下的风,脚步从未停息。齐鲁大地的厚重接住了我。菏泽牡丹盛开,短暂的热闹后,是项目推进中更需细嗅的芬芳。每一次搬迁,行李里塞满的不只是衣物,还有上一个地方沉淀的尘土、汲取的水分和未尽的思绪。巷道深处,矿车的嘶鸣是地下脉搏的震颤,市场交锋的唇枪舌剑是另一种凛冽。我学着在矿山的铁律与街巷的烟火气中寻找平衡,像一盏矿灯里的钨丝,在现实的磨砺中,执拗地亮着自己的光。
而我的生命,也在此刻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——一个新生命在我体内悄然孕育、生长。随着月份渐长,身体变得笨拙而沉重。孕晚期的日子尤其艰难,腰背的酸痛如影随形,双腿也时常浮肿。然而,工作并未因身体的特殊而按下暂停键。那个臃肿的、缓慢移动在办公桌与资料柜之间的背影,成了办公室里最沉默,也最坚韧的注脚。
孩子刚满三个月,我来到了淄博矿区。周末回家时,高铁成了“生命线”。我提着给孩子准备的小礼物,在车厢里和丈夫视频:“宝宝今天会叫妈妈了!”屏幕那头的小人儿挥舞着玩具,而我低头整理时,眼泪突然砸在屏幕上。
2021年,疫情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,封控倏然降临。这一年,我几乎被困在单位,与家人分隔两地,只能隔着屏幕传递思念。隔离酒店窗外的世界悄然无声,我独自伏案工作,灯光下孤独的影子映在墙上,仿佛也静静陪伴着我。然而疫情这堵墙虽阻隔了相见,却未能拦住工作,我在静默中仍然勤勉完成使命,更是在此期间淬炼出非同寻常的坚韧。
公司整合西进,我转调陕西。八百里秦川的黄土,沉淀着千年的厚重。这里的风沙似乎都带着历史的回响。西安城墙的巍峨,不只是风景,更像一种无声的训诫:欲成事,需有根基,需有定力。工作在古都的背景下展开,多了几分沉甸甸的责任。那些挑灯夜战的时刻,与“战友”在办公室围炉煮面抗击疫情的时刻,仿佛就在昨天。窗外的月光与千年前照耀过秦砖汉瓦的并无二致,一种穿越时空的使命感悄然滋生。在陕西,我肩上的担子更重,视野也更开阔。黄土地的深沉教会我回望与前瞻。我像一棵把根须更深扎入大地的树,汲取着矿山的养分,也将绿荫投向更远的地方。青岛的海风与丈夫的叮咛孩子的牵挂,始终是那根系住风筝的长线,让我在黄土高坡上,心有所依,行有方向。
2025年春天,由于工作需要我轮岗回到泰安。高铁穿过熟悉的田野时,手机里弹出孩子的消息:“妈妈,我考了第一名!”我望向窗外飞逝的风景,忽然想起伊宁矿区那盏探照灯,菏泽火车的鸣笛声,淄博口罩下的勒痕……
原来十五年光阴,早已在铁轨上刻下年轮。
如今,我在泰安的办公室整理文件,窗外的泰山沉默如磐。偶然翻到旧照片:大雪中的绿皮火车、菏泽麦田里的矿工帽、淄博防护服上的签名……它们像散落的拼图,拼出一幅名为“成长”的地图。
为矿区服务了一辈子的老工长退休时说:“咱们这辈子,是和铁轨绑在一起了。”而我终于懂得,那些穿梭千里的旅程,不仅是地理的迁徙,更是母亲在时代浪潮中,用柔韧的脊梁撑起的一方天地。
我与山东能源集团,便是在这山河辗转中,完成了最深刻的共生。它的战略版图是我的足迹,我的成长年轮是它延伸的脉络。那些异乡的灯火,照见过孤独,也点燃了信念;那些陌生的方言,曾是障碍,最终成了理解这片土地最亲切的密码。风雪中抵达,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站稳;每一次告别,都是为了更深地融入。历程,是身体的迁徙,更是精神的拓荒。山东能源集团给了我一片驰骋的疆域,而我,以脚步和汗水,在每一寸土地上刻下共同成长的印记。站在泰山脚下,山风浩荡,心中澄明:那些走过的路,遇过的人,攻克的难,都已成为骨骼的一部分,支撑我,也支撑着我们的共同事业,向更高处,行稳致远。